【论教·中国特色高校之道】
光明日报记者 邓 晖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
这既关乎办学,更关乎人才培养,与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密切相关。而落实到细致处,如何遵循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是高校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重要抓手。为此,本版在《论教》栏目中开设《中国特色高校之道》专题,邀请专家学者从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出发,紧密联系高校现实和未来发展,发表见解,启发共识,以为互鉴。
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 邓 晖
对话人:清华大学教授 姚期智
13年前,一个人、一张机票,58岁的姚期智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回到清华大学作全职教授。4000多个日夜以来,创“姚班”(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揽人才、攻前沿,这位迄今为止图灵奖唯一一位亚裔得主做的所有事都紧密围绕着一个中心——创建世界一流计算机学科、培养世界一流计算机人才。姚期智说,这是“翻山越岭”的13年。“翻山越岭”中,他对“两个一流”建设有什么体悟?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有哪些思索?2016年12月29日,记者走进姚期智办公室,与这位计算机大师展开独家对话,这些温热,带着思想火花的文字,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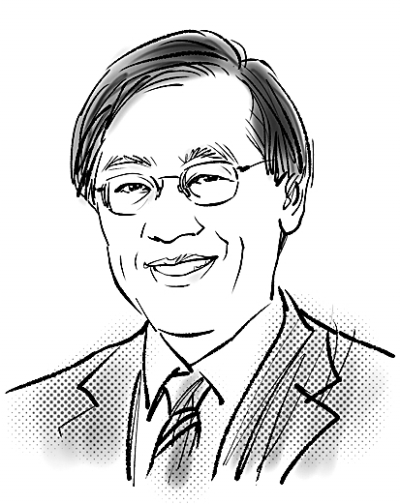
姚期智(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郭红松绘/光明图片
“中国特色”让中国大学有机会迎头赶上
记者:刚回国时,你说常常在想,“一所大学如何能够培养有创造力、有想象力、能作出新贡献的学生”。我们正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一目标该如何理解,怎样去实现?
姚期智:不管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亚洲,世界一流大学有个普遍意义:有相当一部分学科、院系是世界一流的,里面的老师大部分也要是世界一流。如果世界一流的人聚在一起,其他东西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他们不会允许非一流成果,也会想尽办法去培养一流学生、设计一流课程。一流大学可以大,也可以小,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就是一流,像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法学院,但从没人质疑过它是一流。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国外方法不能照样搬来,要想想看中国有什么特殊优势、利用好。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的优势主要有三点:
一是中国有非常好的人才储备。这不但让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容易做得好,也使很多研究工作在中国推进得更快。中国还有很多海外人才,在很多时候能为科研发展提供协助。
二是中国在科研经费上具有很好的优势。中国这几年经济成长非常快,投入到科研上的经费也逐渐增加。这非常重要。因为科研要赶超,一定需要特别的经费来做事。
三是中国在行政上的执行力非常强。这种在行政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可以使我们在想做的事情上特别有效率。我十几年前开始在清华办“姚班”,有很多特别的事情,比如二次招生、独立课程等。如果在国外尤其是一些规则比较成熟的学校,即使这件事特别好,它的障碍也会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除了一些有比较成熟系统的发达国家,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可以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完备的科研、教学高水平体制,来创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中国是一个例外,因为有这些特色,我们能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
建设“两个一流”,要有耐心
记者:你刚才讲到了很多中国特色优势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助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必定会有一些束缚和尚未突破的难点。
姚期智:这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基础的教育教学来说,我觉得已经完成了解放。至少从清华以及其他很多和清华一样比较领先的国内大学来说,很多条条框框已经改善得差不多了。现在更重要的是从教育观点看,怎样让教师有积极性去拓展教学。不是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做这件事,一个学院里能有十几、二十个人把精力很专注地投入其中,而且能合作起来,大学教育就可以办得很好。这涉及一个导向,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奖励方法来构建这样一个团队,去研究当今世界一流的教育教学什么样,而不是把时间用在去外面做咨询等事上。这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临门一脚”。
二是从科研上看。科研上一定要有非常好的人才,一流人才才能领导、培养年轻人,久而久之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些年,国家已经有很大的项目培养、吸引这些人才,但这急不得,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积累,还要有配套措施让他们专心做研究。回国十几年来,我觉得这方面虽然还没有到达一个效率非常高的地步,但也有了很大成效。譬如说在清华,如果一个青年老师的研究水平达到国际水准,他的基本研究经费是没问题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国家最需要的研究方向,能不能快速做起来。现在国家在一些先进、有竞争性和急缺的领域已经在推动比较重大的项目,从这点上来看中国已经到了“内行引导内行”的阶段。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那么理想的状况,但这和发展阶段有关系。如果你在美国推动一个比较前瞻性的科研活动,做起来比中国容易。一是大家距离没那么远,二是如果一个很有威信的人让你来开会,大家都很愿意、甚至自费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一个领域的活力推动起来。但在中国就很困难,因为很多尖端人才不在国内。如果中国在尖端领域比谁都做得好,那么大家即便自己花钱也愿意加入进来,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问题,要有耐心。
好的本科教育要让学生发现喜欢什么、擅长什么
记者:你多次提到“人才”。现在无论清华、北大,还是中国其他高水平大学,都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努力。你回国原本想尽快打造一支好的研究团队,最后却选择了从本科教育开始。几年前我们采访杨振宁先生,他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不比国外差、甚至要好,你怎么看?
姚期智:国内本科生的聪明才智确实是世界一流的,特别是国内一流大学,学生入学时比美国一般一流大学学生都优秀。尤其是在一些我们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上,比如数学、物理,大学教材有很多年积累,跟世界水平没有大差距,这比较容易在教学上做得好。所以从这点上,我同意杨先生的看法。但在计算机学科或别的前沿学科,你会看到美国大学,每过若干年,就会仔细地、大幅度地调整一下本科教育——要从前沿看课程和教材设计里要删去、增加哪些,这样才能使本科的学生对发展前沿有基本了解。如果学科不与时俱进,很容易在学生毕业时有些该教的东西没有教。
这点我在国外大学有很多感受。我经常看到国内来的学生,甚至是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来做研究生时,有一种令人震惊的情况,就是很多该学的没学。还有同样严重的,他们的思维水平和方式不够深刻。但国外研究生的一些课程或考试,并非死记硬背就行。所以那时我就感觉到国内计算机科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缺点:一是很多该教的没有教,二是教学、考试比较注重学生勤不勤奋。真正好的本科教育,是要让学生从中学思维方式转换成大学的研究思维,必须要挑战他们的智力。我一向主张,教育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发现自己最擅长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将来不管就业还是深造,都沿着这个方向去进行。所以一门课不是人人100分是好事。
如果不能让学生发现这些、迎接挑战,就会产生很糟糕的效果——觉得自己不如人,就放低志向,把目标调校成拿到博士学位、找个大公司。我在国外一流计算机系里看到很多印度教授,但中国教授很少。我的感觉是,可能是我们的学生起点不高,所以志向不够。再后来,我回国想要把研究团队建起来,却发现收到的研究生能力不够,开始一年或一年半都在补课。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出世界上最好的本科生,这样才能有足够好的一流研究生资源。况且,面对这么好的生源,如果四年后不能保证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那我们的教育就失败了。
记者:“姚班”是国内创新人才培养的一面旗帜,它可以复制吗?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姚期智:办好本科教育并不难。这个阶段,学生关键是要打基础,只要把核心学好、基础学透彻,课开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教师团队很重要,只要一个院系有10个教授愿意把这件事做好、开好10门核心课程就能办好本科教育,这点中国很多大学都能做到。
当然,这在细节上有分别。在“姚班”,课程难度、教学速度比一般本科生要高和快,学生在大二、大三就基本能达到研究生水平。比如我教的大一的一门数学课,在斯坦福这种学校他们要到四年级才学。对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如果按部就班他们会觉得非常没兴趣,因此在本科时就要尽快让他们接触到科研。
再有考试和作业,要让最好的学生觉得有挑战性、非常过瘾。五门课里,我希望你有三门课学得很好、两门不好,而不是五门平均。因为你到外面做工,人家会问你最喜欢什么、哪方面特别拿手,再指派工作,这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
还有就是对“姚班”学生很重要的全英文教学和足够多的国际交流机会,让他们在整个过程里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国际人才。毕竟,他们将来是要在国际学术圈里和别人竞争,用国际语言和别人打交道。
记者:回国后,你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在国内大学里,很多教授只挂帅不上台,讲课都由助手或者年轻人来做。本该得到重视的本科教学却成了“良心活”,科研才是“最重要”的。
姚期智:一个大牌教授教一门入门的课,是比较好的。他的视野比较广阔,能及时让学生把握到学科方向和定位,所以说资深教授应该教书。这点在美国要求比较刚性,每个老师教课的数量是差不多的。但也有个别情况,如果有时他把时间花在别的地方,对整个学科的成长有更大帮助,尤其是一个大项目刚启动的时候,是可以柔性处理的。我刚回国花在教书上的时间非常多,因为那时还没有足够多的老师,很多课都是第一次开,所以我自己先教。现在形成了一定规模,这方面压力小多了,我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打开学生眼界。
至于本科教育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想这有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离开科技前沿太久,所以那时需要把科研水准快速提升起来。只有科研人员到了一定水准,才有可能教好课,如果根本不晓得科技前沿在哪,就只能教很陈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战术角度来讲,这有其中的逻辑。但现在重心应该要调整一下了,我相信在国家、学校都重视的情况下,做好本科教育应该没有问题。